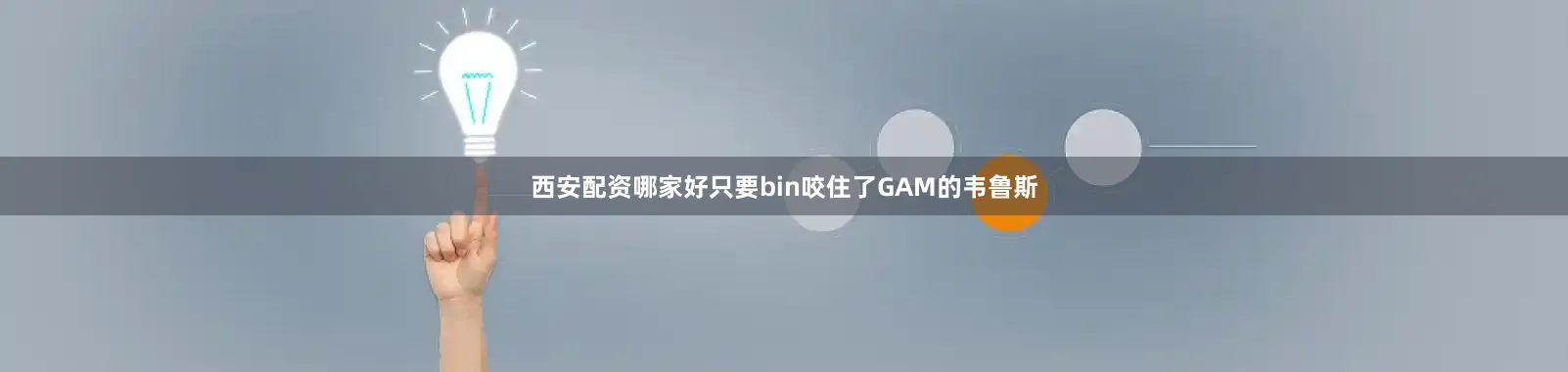新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就,常被世人歌颂,那是国人的无上骄傲。这份辉煌背后,却藏着一支被光芒掩盖的“无名大军”,他们长达六年默默付出。
他们的“做窝”之功,同科学家的“下蛋”之名同样举足轻重,甚至带着一丝悲壮色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免受外强欺凌,国家高层决定发展核武器。
这不单是尖端科技的较量,更是民族意志的硬仗。核心基地的选址,被定在了广袤且荒凉的西北戈壁深处。
这篇文章将揭示,这支代号“无名”的十万大军,如何筑就两弹基石。同时,也讲述率领他们的开国上将,如何在极致艰苦中,坚守清廉与担当,成为这“隐形工程”的灵魂人物。

戈壁筑巢人
1958年,寂静了无数个世纪的新疆戈壁滩,忽然变得喧嚣起来。十万大军在此热火朝天劳作,机器轰鸣,工程车辆穿梭不停。他们的目标,是在这片不毛之地“做窝”。
这一切,起源于1956年4月。钱学森在总参会议上,兴奋地阐述了发展导弹技术的设想,鼓舞了在场的元帅和将军们。
国家随即启动了一系列筹备。1957年秋,导弹试验靶场的筹建工作正式提上日程。到1958年4月,两弹基地建设的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
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今天的世界,有原子弹才有底气。我们若不想被欺负,就必须拥有它。”他还乐观预言:“我们也要搞原子弹和氢弹,我看十年完全能完成两弹工程。”
陈士榘上将被任命为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肩负起为两弹工程“做窝”的重任。他充满激情地投入工作,带着苏联专家和国内勘测设计人员,前往大西北考察。
他们一行人抵达新疆后,乘坐直升机飞越荒漠,发现了几片碧玉般的湖泊,那就是罗布泊地区。考察团队经研究决定,将罗布泊定为两弹基地。
随即,一支代号“7169”的工程兵部队,便开赴了这片神秘的罗布泊区域。建设两弹基地,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大工程。
国家先后调集了十万大军参与建设,包括七个建筑团、五个工兵团、两个建筑师、两个汽车团,还有铁道兵、通信兵、空军建筑分部等多种力量。
戈壁滩的气候变幻莫测,条件异常艰苦。“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吃水贵如油,四季穿棉袄”,这是战士们对戈壁滩的真实写照。

白天烈日炎炎,让人全身灼热;夜晚却寒冷刺骨。狂风常常刮得天昏地暗,卷起漫天黄沙,沙子无孔不入。
即便吃饭时,黄沙也落在饭菜上。帐篷常被狂风卷走,瞬间无影无踪。战士们开动脑筋,尝试栽树种草来对抗风沙。
帐篷被吹走后,他们就用土盖房子,顶棚用草和黄泥密封,虽简陋却牢固。沙漠中水资源珍贵,战士们想方设法收集雪水雨水。
他们格外珍惜水,一盆水先洗脸,再洗脚,再洗衣,最后浇树。建设期间正值困难时期,食物匮乏。陈士榘与五位将军,一同挤在四平方米的土坯房里。
他们吃不饱,也没有蔬菜。陈士榘动员战士们挖野菜、摘骆驼刺补充口粮,但大家仍普遍营养不良。
即便生产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官兵们仍劲头十足。1958年下半年,黄河中下游地区遭遇了自1930年以来最大的洪峰。
这场洪水冲垮了郑州黄河大桥的11号桥墩,导致京广铁路停运,南北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时任河南省委迅速上报灾情,周总理当时正在河南郑州开会,听闻情况心急如焚。
周总理立即指示河南省委:“要想办法解决大家饮水问题,不准死一个人。”他随后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交通部部长吕正操以及河北省委人员一同视察了黄河大桥。
考虑到郑州和新乡滞留了大批乘客,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会议,决定临时修建一座浮桥,供乘客先行离开。同时,出动工程兵抢修黄河大桥。
陈士榘接到任务后,立即抽调四个舟桥团、一个工兵团,以及三个工程兵学校的四个学员连紧急赶赴现场。经过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抢修,工程兵圆满完成了任务。

这次行动,工程兵部队展现了过人的素质,这与陈士榘长期的努力分不开。
将军本色
当工程建设如火如荼进行时,原子弹爆炸试验工程即将进入勘察阶段。主席密切关注大西北的建设,但当时面临一个大问题:通讯不畅。
如何让大漠与北京实现畅通联络?陈士榘仔细思考后,连夜写信给周公,请求尽快解决北京到新疆的联络问题。周公将批示和报告转给了财经委员会的薄主任。
薄主任有些为难,因为这将是一条当时全国最长的专用通讯线路,而国库库存的铜线不多。薄主任对陈士榘说:“国库里只有五吨铜线,你看够用吗?”
陈士榘回答:“这么多铜线已经很好了。”薄主任一听,高兴地说:“那五吨铜线都给你了。”一条金色的长线,从北京穿越无垠大漠,经过酒泉基地,直至乌鲁木齐。
线路接通后,陈士榘第一次用这条专线向周公报告。周公说:“好,有了这条线路,我也相当于到了你们的第一线。”
1959年,导弹试验进入选择投弹地点的阶段。大家决定将投弹地点定在罗布泊。罗布泊被称为死亡之海,广阔而神秘,只有通过飞机才能更直观地探测。
陈士榘找到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请支援我们一架飞机勘测投弹地点,要尽快。”刘亚楼爽快回应:“这是大事,我一定全力配合,把性能最好的飞机给你。”
在飞机上,陈士榘坐在飞行员和机械师之间,以便观察得更清楚。飞机连续飞行了三个小时,眼前尽是荒漠。

当一条峡谷出现在面前时,陈士榘要求进去看一看。飞行员表示很危险,但陈士榘强调核试验的重要性,坚持要进去。
飞行员驾机飞进了深谷,谷内一片阴森,大家有些紧张。飞机猛然抬头,冲出了一个山垭口,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广阔的塔里木盆地。
这片区域广阔无垠,非常适合投弹。陈士榘非常高兴,称赞飞行员技术娴熟,胆量超群。这次飞行圆满完成了勘察任务。
将军家风
陈士榘的身体原本就不好,在缺水少食的环境下,他的病情更加严重。有时,他极度劳累后,还需要往返于两个建设基地之间视察。
他甚至一度晕倒在建设基地。然而,即便如此,身体稍有恢复的陈士榘,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程建设当中。
前后六年时间里,陈士榘与他率领的工程兵部队,吃尽了无尽的苦头,最终完成了建设任务。然而,这位身居高位的将军,在生活上却清贫得让人难以想象。
他的月薪原本有430多元,作为开国上将五级干部,待遇不可谓不高。但后来,主席带头减薪,只拿四级工资以缩小贫富差距,其他领导干部纷纷效仿。
陈士榘也主动减薪,只拿342元。虽然这在当时仍是笔不小的收入,但对于他有六个孩子、一个养女,上面还有一个老人的家庭来说,开支巨大。
家里的几个孩子正值长身体的时候,经常喊饿。陈士榘就在自家小楼前的一片空地上养了一头猪,因没有饲料,养到四五十斤重时便宰杀,还会分给周围的邻居一些。

陈士榘的秘书李柱江回忆道,陈司令孩子多,所以他也要节衣缩食,家里的生活水平也就刚够温饱。
陈士榘将军的公私分明,可谓刻入了骨子里,到了“格式化”的程度。他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乘坐火车本可以用一个包厢。
包厢里有四个软卧,而其他秘书就只能坐硬卧。但他每次都坚持让秘书们住包厢,一来能让他们休息好,二来也是为国家节省开支。
有一次,秘书代陈司令去领工资,结果发现少了26元。秘书去核对时,财务告知:“陈司令用了一次中吉普车,是他让财务把费用从工资中扣掉了。”
1963年,陈人康随父亲陈士榘到沈阳军区,当地部队首长提出可去打野鸡改善生活,陈士榘直接拒绝:“没有这个爱好,还是赶快下部队吧。”
到长春后,市委工作人员安排参观长春电影制片厂。陈人康对此颇有兴趣,悄悄对父亲说:“去长影多好啊。”
哪知陈士榘头也不回,一口回绝了儿子的提议:“我们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长影就不去了,到一汽去,因为我们部队要用很多一汽的车,我要和他们探讨怎样生产工程兵更适用的车。”
陈士榘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家里的孩子同样如此。陈人康回忆,妹妹陈小琴的学校离家有十几里,每次来回走很费时间。
有一次生病发烧,女儿向父亲提出希望能用车送一下。这本是很小的要求,结果不仅没坐到车,还被父亲责骂了一顿:“车是给我用的,不是给家属用的,老百姓的孩子生病就不会想到用车?”
还有一次,妹妹陈小琴向父亲索要一块怀表。这怀表是陈士榘早年在抗战中缴获日本军官的,一枚镀18K金的怀表。

妹妹索要,并非为实用,而是看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总揣着怀表,出于一种英雄情结。结果自然又被父亲训斥了一顿。直到1979年妹妹考上大学,父亲才郑重地将怀表交到她手里,并题字:“好好学习,振兴中华。”
六十年代初,几个孩子参加国庆烟火晚会,在观礼台附近捡到一个烟花降落伞,都很高兴。结果带回家后,又被父亲批评:“公家财产一分钱也不能沾。”
在陈士榘的严格要求下,孩子们把降落伞送到了工程兵军务处,同志们笑着说:“陈司令对你们的要求也太严格了些。”
尽管陈士榘有很多老战友的关系,但却从未为自己的子女动用过。八十年代初,部队摸底高级干部家庭子女经商情况。
陈士榘坦然表示:“我除去两个儿子没有工作,其他都是正式单位的职工。我已经没有权力可用,有权力也不会给他们用。”
戈壁定乾坤
中国的核物理研究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8年9月27日,媒体发布消息:北京郊外的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
这标志着中国的核物理研究已经走上正轨。这条消息,让建设基地的十万大军非常激动。战士们兴奋得夜里睡不着觉,纷纷议论:“我国人就是聪明,能成事!”
他们还说:“核物理创造奇迹,我们工程兵也要创造建设基地的奇迹。”随后,核物理工程的速度一再加快。
从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部队共创造发明了2950多项。其中,7439部队创造了万能工具台,替代了过去仅有的9种电工机具。

0215部队发明了外部装药爆破法,大大提高了功效,并节省经费53万元。当中国军事、建筑等各方面发展进入正轨时,苏联却单方面撕毁了技术协定。
他们撤走了在中国的所有专家,半路撂了挑子。陈士榘气愤地说:“依靠别国的力量肯定不长久,我国人不怕别人卡脖子,一定能挺直脊梁。”
两弹基地的首期工程分布在1.3万平方公里的41个厂区,包括机场、铁路、公路、特种营房、电力、通讯及排水设备安装等工程。
陈士榘指挥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争分夺秒地施工,历尽艰辛。终于在1960年8月,提前三年完成了工程建设任务。
国防科工委组织专家对工程逐一进行质量检验,专家们称赞工程加速度完成且质量过硬。首期工程恰好赶在苏联撕毁合同之前完工。
因此,苏方只得按合同交付了全套设备。提前三年完成工程并抢回了设备,难怪陈士榘在苏方撕毁合同后能有底气地说话。
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七天,1960年9月12日,中国使用自主研发的燃料发射了第一枚地弹,并获得成功。11月5日,中国发射了由国内科学家制造的第一枚导弹。
当天上午9点,随着点火一声命令,火光闪耀,轰隆巨响。在众人焦急等待后,传来消息:国产导弹已坠落到预定目标。担任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上将高兴地跳了起来,陈士榘激动喊道:“我们的工程建设质量可靠!”
1964年10月16日15时,新疆戈壁滩上空出现一道强烈的火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紧接着是惊天动地的巨响,火球随即变成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大约十分钟后,张爱萍用激动的声音,向等在北京中南海电话机旁的周公报告:“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此时,专家们正忙碌地从1700多台测试仪器上记录首次试验的效果,拿到了97%的数据。

相比之下,美国、英国、苏联在第一次核试验时,仅拿到了很小一部分数据。当周公庄严宣布中国成功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消息时,举国欢呼沸腾,全世界震惊。
1964年,首都军民新年联欢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席紧紧握住陈士榘的手说:“祝贺你们做窝成功,你们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
毛主席还在一次联欢会上,高兴地握住张爱萍和陈士榘的手说:“祝贺你,你们(指工程兵)立了功。他们(指国防科委)出了名,你们做窝(指建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指爆炸原子弹),你们立了大功!”
当两弹一星对外公布后,世人都知晓了钱学森、邓稼先等爱国科学家的无私奉献,却很少有人知道工程兵部队建设两弹基地的事。
这十万人的部队,从1958年4月到1964年9月,在戈壁滩上战天斗地了六年多。这项任务属于严格保密的行动。
战士们从戈壁滩撤出时,每个人身上一片纸都不许留,所有工作笔记一律上交,仿佛这六年从未有过痕迹。
陈士榘在他的回忆中,提到这十万人的部队时,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他说:“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我的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
笔者以为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个艰苦创业的时代,他们为中国军事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陈士榘晚年时身体已欠佳,尤其是几次心脏病发作后,身体状况几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1995年4月,陈士榘迎来86岁生日。

几位老同志提议为将军祝寿,有关部门也表示同意,只需做个预算,再由陈士榘签字即可。工作人员做好预算单,拿着找将军签字:“陈司令,给您做寿,您看看需要改进什么?”
陈士榘强撑病体坐起来,戴上老花镜仔细审视预算单,眉头一皱,很不高兴地说:“这是谁让这样搞的?”“这是大家的心意。”
“大家的心意?”陈士榘摇摇头,生气地说:“我陈士榘什么时候这样干过?不要因为生日把我一生的作风改变了!我们党历来有纪律,不能用公款请客吃饭,我一辈子都遵守了。”
“明知有纪律,还写报告要钱,这是给军委领导出难题啊。”“我听说全国公款请客一年就要花去上千亿元,这还了得?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绝不是为自己享受的。”
陈士榘还给众人讲了一个故事:民国年间,冯玉祥将军廉洁奉公,拒绝奢侈。有个下属给他送来一坛清水,冯玉祥非常高兴,还告诉身边的人:“清水是人最需要的,也最便宜。”
冯玉祥是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诫下属:“为官要像水一样清白。”“我们共产党人为解放牺牲了那么多优秀的儿女,如果他们知道最终有一些领导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如果不从严治党,这样的人会把我们党搞垮,人民群众也会抛弃我们。”过生日当天,陈士榘与几名老战友围坐,秘书按他吩咐端来一坛清水,几人以茶代酒,谈天说地。
陈士榘在众人的祝贺中,度过了他人生最后一个生日。核爆的蘑菇云最终腾空而起,震撼世界,为中国赢得了尊严。
然而,这背后无数无名英雄的青春和生命,以及陈士榘等指挥者的清廉与担当,如同戈壁滩上的风沙一样,被历史所“掩埋”。
他们是国家的隐形脊梁,是“自力更生”精神的具象化,用血肉之躯在荒漠上筑起了民族复兴的基石。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功勋,更是对后来者关于责任、奉献与清廉的深刻启示。
伯乐配资-配资门户平台-最好的证券公司-南宁配资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网app官方免费下载安装指数股票型基金排名164/2954
- 下一篇:没有了